借鉴古洋寻我法——杨之光的人物画实践及其相关问题

杨之光 傣族蜡条舞 70×46厘米 1990
杨之光(1930—2016),又名焘甫,男,汉族,生于上海,广东揭西人。1949年入广州艺专及南中美院,1950年入苏州美专上海分校中国画科学习,1950年夏考入北京中央美术学院绘画系。历任广州美术学院国画系教授、系主任、副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广东分会理事,曾任岭南美术专修学院院长等职。代表作有《毛泽东主办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浴日图》《矿山新兵》《激扬文字》等。著作有《中国画人物画法》《杨之光画集》《杨之光书法集》《杨之光诗选》等。2013年1月获第二届“中国美术奖·终身成就奖”。
今年初夏,杨之光在广州离世。由于广州美术学院教授李伟铭对杨之光做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因此本刊谨以此文向大家介绍“时代人物”杨之光。(文/李伟铭)

杨之光
广州,2016年5月14日19时30分,86岁的杨之光,终于摆脱多年疾病的折磨,走了!斯人已逝,艺道长存——他带走两袖清风、乐于奖掖后进的为人风度,却给这个世界留下难以估量的精神财富,以及中国画艺术在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进程中无法回避的种种问题。在这里,我想用这篇小文,记录面对“杨之光现象”的思考,同时,再次表达我对这位锲而不舍的中国新人物画艺术的探索者崇高的敬意。

1950年,杨之光临摩壁画
在许多场合,杨之光多次提到在其艺术生涯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两位老师:高剑父和徐悲鸿。其活动年表告诉我们:上世纪40年代末,杨在上海完成中学教育之后,持书法老师李健先生的介绍函南下广州拜高剑父为师;50年代初,经颜文樑先生推荐,北上进入中央美术学院,在徐悲鸿先生主持的这所学校完成了大学本科学业,之后一直在广州美术学院从事教学工作。在写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一份回忆录中,杨之光再次肯定了来自高、徐两位先生的感召力。所有这一切,足以证明,正像他这一辈人中的许多艺术家一样,杨之光对老师的教诲始终持有虔诚的敬意,这种敬意固然合乎传统的道德义旨,同时,也以其特殊的方式,描述了某种观念和知识承传转合的轨迹。

1961年,杨之光体验生活与女民兵在一起
关于高剑父和徐悲鸿之间的接触以及艺术变革方案的异同、在过去和当代中国的命运,我在其他场合已有讨论。在这里可以约略提到的是,就高、徐共同信守的画学变革观念而言,前者似乎更适合称之为“得风气之先”的先驱。民国初年,高氏兄弟通过《真相画报》揭载的那些在今天看来不无粗浅的中西美术知识,以及他们在写实主义的语言结构框架中试图调和中西画法的实验之作,曾给徐悲鸿留下了深刻印象。〔1〕因此,徐悲鸿在稍后赴日期间获得的对近代日本绘画的观感,与高氏兄弟并无二致。换言之,表面上看来,徐悲鸿早年提出的中国画改良方案,只是直接来自康有为关于同一问题的观点的转述;但是,我们至少必须承认,高氏兄弟在这里早已起到了重要的“引介”作用。徐氏后来到欧洲学习,甚至可以视为对高氏兄弟尤其是高剑父一直渴望但由于种种原因的凑合而无法实现的理想的补偿。

1978年,杨之光在河南写生
当然,明确地把学习西方写实绘画以变革中国画作为一个方案,并以文本的形式公诸于世者,首先还是康有为和陈独秀。〔2〕在许多康、陈的当代评论者看来,康有为和陈独秀是造成近百年特别是上世纪50年代以来写实主义绘画在中国美术界“横霸天下”局面的“始作俑者”,他们之贬损文人写意画和对写实绘画狂热的向往,完全源自他们对传统画学的无知。这种明快的判断,正像我们所看到的,也经常被引申到对高剑父和徐悲鸿的评论中,并理所当然地被当做衡量他们艺术成就高低的重要标准。事实是否如此,容当别论;但有必要指出的是,对康、陈这一类思想家的传统知识涵量的估计,最好持谨慎态度;而且,康、陈持论义旨是否相同,尤需加以认真讨论。[page]

1980年,杨之光在宁夏写生
20年前,笔者曾在《康有为与陈独秀——20世纪中国美术史中的一桩“公案”及其相关问题》〔3〕一文中,对康、陈的异同有过粗浅的分析,在这里我想再次强调,康、陈方案发表的时候,前者作为背气的晚清遗老正在重调虚君共和的老调,倡言捧孔教为国教;后者作为激进的自由主义思想家,则把打倒“孔家店”当做为科学、民主的引进和发展扫清道路的头等大事。正像在意识形态上把科学、民主看做与孔教的传统无法相融的现代意识一样,陈氏的美术革命论具有强烈的文化整体论色彩;康氏恰好相反,不但把写实绘画看做一种已然存在的传统,轻而易举地把“合中西而为画学新纪元”的理想纳入其“以复古为更新”的思想框架,而且,在形而下的层次——“工艺之学”的角度——把调和中西的写实绘画,看做一种可以直接丰富日常器用生产的物质力量,进而顺理成章地呼应了他在早些时候提出的“物质救国”主张。〔4〕

1990年,杨之光在美国康州作画
显而易见,在康、陈表面上看来似乎完全相同的美术变革方案中,实际上存在着完全不同的逻辑结构和价值指向。高剑父和徐悲鸿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认同陈氏的方案,迄今为止仍然是一个缺乏充分研究的问题;综观高、徐的绘画实践,似乎很容易得出以下结论:在文化建设中,高剑父和徐悲鸿绝对不能归类于全盘性反传统主义者的行列。暂置康氏提案中的物性功利意识勿论,较之陈氏推举白话为文学正宗时,那种毅然决然“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余地”的独断,〔5〕康氏对传统绘画始终抱持谨慎的敬意,无疑更能够获得高、徐这类既不想担当背叛传统的罪名,同时,又希望传统的美学标准在新的文化情境中有所修正和发展的艺术家的认同。

1995年,杨之光四十年回顾展艺术研讨会
从强调绘画的社会教化功能这个角度来看,即使没有文学革命潮流的激荡,高、徐仍然能够直接从康氏的学生梁启超及其盟友无限夸大小说革命的社会政治功用的学说中获得足够的教益;何况在源远流长的古典画学传统及其现代转型的过程中,“明劝戒、著升沉”之说一直没有中断。如果说,高剑父和徐悲鸿关于中国画改良的认识有一点与陈氏的美术革命论比较接近的话,那就是,至少在他们看来,在历史新、旧交替之际,倡扬建立在西方透视学和解剖学基础上的写实画法,是克服传统中国画习惯于案头辗转临摹的积习唯一明智的选择。高、徐调和中西画法的具体方法容有差异,他们的艺术观点随着情境的变迁也时有修正,但总的来说,这一基本观念始终未变。当然,高、徐的艺术风格明显不同;但与其说这种差别源自艺术观念的歧异,倒不如说源自知识结构的不同。而且,也许没有什么比高、徐给予杨之光的入学训示更能够反映他们的知识结构特点:高氏在传统的画法体系中获得了更多的传统笔墨的训练,其“调和中西”,始终难以消除近代日本绘画中的京都情结;〔6〕徐氏在欧洲接受了系统扎实的学院派训练,其“调和中西”画法的知识支点主要是西方的古典写实主义传统,因之,后者具有更为强烈的理性自觉。杨之光在高氏门下渡过的时光(1948年冬至1949年夏),只是其学生生涯中一个短小的插曲,作为一位写实人物画家,他的基本造型能力主要还是得自徐悲鸿及其中央美术学院的同事的调教。而较之徐悲鸿精严的学者风度,高剑父可能更为开放的实验精神则显然给杨之光留下了更为深刻的印象。因此,尽管杨之光在中央美院学习期间,传统画法的练习只有白描一科,但如何使传统的线条风格与西方的写实造型语汇在一种新的语言结构中获得整合,从追踵高剑父那一天开始,对他来说就是一个具有巨大魅力的课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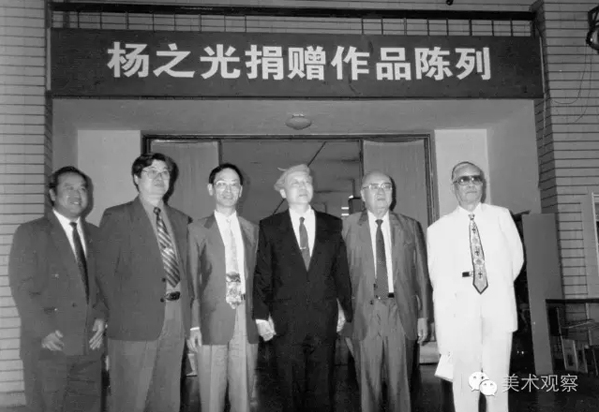
1995年,杨之光向中国美术馆捐赠作品
应该承认,高、徐努力的成效,已经以不同的方式为杨之光提供了丰富的经验。但是,高氏的实验范围主要在花鸟画,其“折衷中西”,在晚年已呈现了向传统复归的倾向;即使是徐悲鸿这位在他的同辈人中具有无可非议的写实造型能力的大师,在解决“调和中西”的难题时也仍然没有达到水乳交融的境界——尤其是表现在写实人物画方面,始终难于超越顾此失彼的两难状态(最突出的证例,可能是其作于1949年的那件《在世界和平大会上听到南京解放》的水墨设色画)。倒是在蒋兆和那里,悲天悯人的中国情怀和冷峻的社会批判意识,有效地冲淡了在调和以线求形的水墨风格和素描的明暗体积结构的实验中出现的不无生硬、粗糙之感。杨之光完成于50年代初期的成名作《一辈子第一回》表明,他最初努力的成效得自蒋兆和的视觉风格的启发。

杨之光 一辈子第一回 101×63厘米 1954
在中国画学的现代变革中,“调和中西”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更重要的是一个文化认同问题。除了吴冠中先生(吴氏晚年有一个引人注目的论点:笔墨等于零),绝大多数介入这场旷日持久的实验与论战的艺术家包括他们的评论者,都认为“笔墨”是中国画之所以为中国画的灵魂,“底线”之说俨然成为中国画艺术最后一道防线上的堡垒。〔7〕笔墨决定论可以在所有的传统文人画理论中找到它的根源;但把“笔墨”与以素描为基础的西方造型体系对立起来,赋予“笔墨”至高无上的精神特质,毕竟是近百来的事情。按照一战以来开始在中国广为流行的说法或“定义”: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是精神文化,西方文化是物质文化——精神高于物质,西方写实画法只能尽物之性而无法充分自由地抒人之情;传统的写意笔墨作为独立自存的表现体系,不但具有超乎形骸之上的审美价值,而且,作为东方文化的载体,本身就是东方精神文明的象征。东方精神文明优胜论,可以在印象派以后某些西方画家不同程度地接受了东方绘画中的线条风格的影响这一事实中找到论据,在下述传说中也能够获得证验:20世纪前期,不少留学西洋的中国画家,据说曾被他们的老师告知:真正的艺术在中国。〔8〕[page]

1996年,中国美术馆举办“杨之光捐赠作品陈列”展留影

杨之光 毛泽东同志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 64.5×89厘米 1959
无论是高剑父、徐悲鸿这一类折衷主义者,还是决心捍卫传统的纯洁性的艺术家,他们都深深地受到了战后这一思潮的感染。30年代初年,高剑父在印度与著名的亚洲精神主义者泰戈尔会面的时候,就曾经充满信心地指出,西方世界如果打算在被野蛮的物质文化摧毁的废墟上重建他们的精神家园,就必须虔诚地接受东方精神文明的洗礼。〔9〕因此,完全可以这样说,上世纪20年代以来,在中西绘画的比较分析中频繁使用的“写意”与“写实”、“表现”与“再现”、“主观”与“客观”、“抽象”与“具象”等成对概念,都植根于这一思想背景。正是在这里,“重道轻艺”的传统价值观再次显示了顽强的生命活力。从逻辑上来说,既然老庄的虚静无为和崇尚自然在文化心理上可以为抗击西方理性主义的挑战提供屡试不爽的有效武器,所谓“笔墨”在观念上也就具有了自我防守的价值功能。50年代初期,“彩墨画”这一概念的强制流行虽然大有取代源自日文的“国画”一词之势,但毕竟昙花一现。事实证明,折衷主义的文化哲学不仅在过去、在新的文化情境中仍然持续有效;而且,只要其价值功能合乎“现实的需要”,就完全有资格在当代中国成为艺术上的“新正统主义”的代表。

2003年,杨之光从教50周年纪念活动在广州美术学院举行

杨之光 农会财政部长 43×29厘米 1960
关于“新正统主义”的定义,笔者在此前论述高剑父以及关山月的艺术所以生效的政治、文化机制的时候已经有所揭示,这里不拟赘述。我想指出的仅仅是,包括杨之光在内,上世纪50年代从美术院校毕业走进画坛的中国画家,不管主观条件如何,实际上他们都在被设定的价值结构框架中工作。以杨之光1959年完成的《雪夜送饭》为例,使“雪夜送饭”这一特定的情景氛围得到再现的是近乎精确的焦点透视法——在地平线处隐约闪烁的夜耕灯火,呼应了前景的送饭人物;在使用“立轴”这一传统形制的时候,杨之光还灵活地借鉴了传统折枝图式的“S”形构图方式。据说,这件作品的创作灵感来自杨之光下放劳动中的速写;但为杨之光带来声誉的,并不仅仅是他恰如其分地歌颂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昂激情,更重要的是,在蒋兆和之后,他以卓越的成果进一步证明:素描与传统的视觉惯例,并不总是水火难容。显然,较之师辈,杨之光和他的同代人较少潜在的文化心理障碍,他们是更为讲究实效的一代,他们在生活上彻底地“大众化”,他们那种具有实录性的速写日课,已经有效地缩短了语言与母题之间的技术距离。如果说,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前期,黄胄以其迷人的塞北风情开创了把速写自然流畅的笔意引入水墨重彩人物画,从而开拓了现代写实人物画的新天地的话,那么,杨之光包括刘文西、方增先这些习惯被称之为“学院派”的新中国人物画家,则在解决素描与水墨线条风格如何协调的实践中,把师辈的成果推进了一大步。

杨之光 雪夜送饭 288.5×119.3厘米 1959
显而易见,作为一位中国画家,杨之光确立其风格力量的独特条件,在于他在水彩画方面长期积累的素养(50年代,他在广州美术学院曾担任了一个时期的水彩画教研组组长)。一般来说,相对素描明确的结构界定而言,水彩与传统水墨之间的边界更为蒙糊。通览其绘画创作,很容易看出,杨之光不断尝试发掘水彩画的潜力,他在用色、用墨方面特有的透明感,他之特别倾注于时空氛围的营造——例如《雪夜送饭》、《天涯》(1984年),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水彩”某些表现特质的渗透。耐人寻味的是,除了少数的全盘西化论者,作为中国文化现代化的主流倾向,在理论和实践中无论采取哪种方式强调向西方学习,强调“民族化”总是自觉不自觉地被视为同一问题的两个侧面,杨之光当然也不例外。其迷恋传统水墨大写意风格的魅力,在60年代初期完成的《浴日图》中得到最为充分的证验。与曾经成为时尚的“新文人画”不同,杨之光在强调线条的书法性意味的同时,仍然没有放弃没骨笔法可能具有的潜在“写实”特质——为了证明他的试验来自传统画法的启示,他解释过,《浴日图》中描绘甲板在落日的余辉中闪烁光影的笔触,直接借用了齐白石画虾的那种令人叹为观止的线条笔法。

杨之光 浴日图 117×95厘米 1962
60年代初期这种成功的试验,被杨之光广泛延伸到以后的创作实践中。完成于70年代初期至80年代的一些主要作品——例如《矿山新兵》、《激扬文字》(和鸥洋合作)、《天涯》(和鸥洋合作)——反复证实了水墨写意画法兼容素描光影效应的可能性。或许,《矿山新兵》中的女性形象吹弹得破的皮肤质感,有悖于“现实主义”教条的嫌疑,但是在那个特殊的时代,这件作品的横空出世,无疑有效地强化了杨之光向往的“调和中西”的信念。正是源自出类拔萃的写实能力的自信,使杨之光从80年代开始连续完成了大批名人肖像画。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作品可能应推《蒋兆和》(1982年)、《赵少昂》(1984年)和《石鲁》(1990年)。所有这些对象都是杨之光特别熟悉的人物,因此,他的写实笔法再现的就不仅仅是表面形体的准确。蒋兆和先生曾用“似我非我”这个传统术语来描述杨之光在肖像画艺术中介入的移情功能。从旁观者的角度来看,《石鲁》确实淋漓尽致地表现了事后对石鲁这位20世纪中国画艺术中的悲剧性天才精神面貌的深刻理解;2005年完成的《恩师徐悲鸿》,则可以说是杨之光新人物画实践的“绝唱”。[page]

杨之光 矿山新兵 纸本设色 131×94厘米 1971
杨之光曾经反复强调在运动中把握人物动态、神情和以默记速写的方式训练写实基本功的重要性。这种注重“直接反应”的方式,可能比较接近印象主义的经验;在传统的绘画理论中,也不难找到相近的论述。拘泥于静止状态的描绘以把握对象在空间中的形体结构的精确性,是西方古典写实画法难于与东方式的直觉把握完美吻合之处;即使是蒋兆和先生,似乎也没有成功地走出这种“先天性”的语言禁锢。50年代初期,徐悲鸿在点评杨之光的一件素描作品的时候,也以另一种方式,大略指出了这一点。因此,“直接反应”的方式可能意味着在折衷主义的写实体系中对某种超乎对象之上的精神自由和个人价值的向往。这种向往,在杨之光完成于90年代的那些以舞蹈为母题的作品中,得到更为具体的展现;他的倾向直觉的选择使传统的线条风格的发展获得了更为自由的空间。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舞蹈作为一种形体语言,在空间中的位移变化本身就具有流动的韵律节奏,其与传统书法艺术之间的亲和关系,早在唐代杜甫描写“剑器”的名篇中已得到富于奇迹感的渲染。在这里,杨之光只不过是以绘画语言的形式再现了这种东方式的想象力。

杨之光、鸥洋 激扬文字 96×135厘米 1973

杨之光、欧洋 不灭的明灯 96.5×131厘米 1977
来自西方的写实观念不仅被高、徐及他们的追踵者视为一种珍贵的经验,在20世纪那些被称之为“传统派”的艺术家那里,我们也能够看到这种观念不同程度的微妙影响。〔10〕总的来说,后者对这种“西方的挑战”的直接反应,是自觉地拿起了“唐宋传统”的武器,把“写生”作为抵消近世“空摹之格”的负面影响的不二法门。因此,无论是在更早的任伯年,还是稍后的齐白石、潘天寿那里,我们都能够看到,他们已经成功地消除了“两点是眼,一划是鸟”的积习;尤其是齐氏的水族草虫写生,仅就“写形”而言,完全可以与西方写实画法所达到的精确的再现功能相持并论。也许可以这样假设,齐白石既然可以用寥寥数笔完美地再现一只虾圆活通剔的生命特质,同理,传统的没骨画法当然也能够在水墨写实人物画体系中找到其应有的位置。杨之光近年在人物画实践中所做的大量的没骨画法试验,实质上就是这种假定的确证和延伸。不过,与齐白石不同,杨之光倾向于在水彩画法与传统的线条风格之间寻求适可而止的契合点,为了强调母题的结构、质感,线条的书法性意味必要时也会自觉地减弱。这种微妙的差异,可能正是希望通过“调和中西”的方式来寻求中国画艺术的现代转型的艺术家,有别于在传统的基础上实现传统的创造性转化的艺术家分野之所在。

杨之光、欧洋 天涯 178×97厘米 1984

杨之光 画家赵少昂 68×46厘米 1984

杨之光 石鲁像 纸本设色 69×46厘米 1990
在60岁按时退休那一年,杨之光应美国康州格里菲斯艺术中心(Griffis Art Center)之邀,赴美进行为期一年的研究工作,之后,他又经常在欧美之间穿梭参观考察。活动空间前所未有的拓展,使杨之光获得了充实、校正关于西方传统绘画知识的机会,其直接承传于高剑父、徐悲鸿的“调和中西”方案,也在一种新的文化情境中开始了谨慎的调整。在格里菲斯艺术中心,杨之光深深地感受到了两位分别来自美国和德国的现代派艺术家的魅力——据他说,他在这一时期完成的部分作品,就尝试吸纳了西方抽象艺术的某些手法。具体来说,这种尝试改变了杨之光信守的绘画时空概念。例如在康州完成的《傣族腊条舞》(1990年)、《翻腾的云》(1990年)以及稍后在国内完成的作品如《现代舞印象》(1992年),与此前的代表作比较,杨之光在背景中加进了一些在虔诚的写实主义者包括传统的清规戒律的守护者看来也许是毫无道理的涂抹,前景被推入背景甚至在空间的错位变形中产生了结构的叠压,空间的容积感甚至完全被取消了。杨之光的立意很明显,他不希望观众把母题看做一种可以在生活中获得直接还原的视觉符号,他主要是——也仅仅是,希望这些经过重建的空间结构,有助于在视觉上强化母题引人注目的形式美感。正像《翻腾的云》题称已经给出的诗意诠释一样,观众可以把舞者和道具看做在气流中飘浮的云彩,也可以用敏于感受天籁的心智,在与形式和谐的共鸣中,体验无所不在的大自然的呼吸。[page]

杨之光 翻腾的云 80.5×68厘米 1990
熟悉杨之光的人都知道,“借鉴古洋寻我法,平生最忌食残羹”是常年挂在杨之光画室的座右铭;“酌奇而不失其真,玩华而不坠其实”,则是杨之光经常乐于使用的自用印。可以肯定,杨之光是在写实主义的立场使用《文心雕龙》中的“真”、“实”这对概念。在杨之光看来,虚空臆造,并非理想合适的栖居之所;被感知世界有其独立自存的自在性,尊重或者说忠于这种自在性,是有节制的艺术想象力赖以驰骋的基础。换言之,杨之光从来不准备无条件地放纵想象力的能量而失去对前者贴切、准确的把握。这种对客体宗教般的虔诚,恰好再次显示了高、徐两先生——特别是后者巨大的精神感召力。因此,我想特别强调,以上分析,只限于某种传统的承传转合的把握;调和中西绘画的某些经验以追求“写实”画法的再现功能,只是现代中国流行的折衷主义文化哲学中的一种价值取向。20世纪以来,折衷主义不但容纳了高剑父、徐悲鸿的变革方案,而且,也涵盖了林风眠一类的艺术家的理论和实践。正像塞尚、马蒂斯之不能见容于徐悲鸿一样,某种理论或方案一旦被设定,同时就具有天然的排他性;肯定排它性,意味着在共同的文化背景中,我们对学术独立、风格差异的理解和宽容。正是从这种意义上,我们把康有为、陈独秀以及陈师曾、黄宾虹关于中国画如何获取发展的动力的不同提议,看做具有互补意义的积极的文化建设纲领。

杨之光 现代舞印象 72×100厘米 1992
不同种族之间的文化交流、融合是一个具有世界意义和巨大魅力的命题。就我们所处的情境来说,在20世纪初叶,由那些充满使命感的思想家提出,并经众多艺术家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方式进行探索实践的中国画变革方案,仍然具有实验意义——高剑父和徐悲鸿包括蒋兆和的接力传承者杨之光的工作也不例外。正像贡布里希所说:“如果每一个艺术家都丝毫不师承前人,都能摸索出一套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再现周围世界的方法,我们就无法研究艺术的发展史。要塑造一个为公众所接受的艺术形象,艺术家必须学习和发展前人的创作手法,正因为如此,才有了所谓的艺术史。”我们注意到,贡布里希在重申他在《艺术与错觉》一书中提出的这个观点时,又接着写道:“革新和变化通常是缓慢进行的,所以我们在研究任何一种风格传统时都能寻根溯源。”〔11〕毫无疑问,关注现状、展望未来,与保持清醒的历史感并不矛盾——我的意思是说,没有任何文化或者某种艺术形态能够完全建立在传统的废墟上。在中国现代绘画史中,“守常”与“求变”是一对耐人寻味的概念;尊重个体的选择和保持足够的好奇心,是使我们的现代文化建设事业拥有足够活力的保证。作为五四新文化传统的得益者,我们感到自慰的是,从杨之光这里,我们不但能够看到康、梁一代的折衷主义者颀长的背影,而且,能够倾听到激进的自由主义思想家陈独秀穿越时空的呼声:关注个人价值。
2016年6月1日重订旧稿于青崖书屋
注释:
〔1〕《悲鸿自述》,《良友》第46期,1930年。
〔2〕康有为《万木草堂藏画目》,《康有为先生墨迹丛刊》(二),中州书画社1983年版;陈独秀《美术革命——致吕徵》,《新青年》第6卷第1号,1918年1月。
〔3〕原刊《美术研究》1997年第3期,收入《传统与变革——中国近代美术史事考论》,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
〔4〕参阅康有为《物质救国论》,广智书局,清光绪三十四年二月。
〔5〕参阅胡适《白话文学史·引子》,岳麓书社1985年版;陈独秀《答胡适书》,姜义华主编《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32页。
〔6〕高剑父以文人画笔法写兰、以折衷法画南瓜为杨示范,同时,又借给杨《景年花鸟画谱》和《梅岭画谱》,要求他从勾勒临摹入手;徐悲鸿则一开始就告诉杨,收起过去的习作,从零——从三角、圆球石膏素描学起。参阅《平生最忌食残羹——杨之光回忆录》(岭南画学丛书编委会编《杨之光四年回顾文集》,岭南美术出版社1995年版,第111、115页)按,《景年花鸟画谱》初版于明治二十四年(1891年),作者今尾景年(1845—1924),早年曾从浮世绘师梅川东居学画,后来师事铃木百年,明治十三年开始在京都府画学校担任教职。其人擅长花鸟写生,画风流丽、优美,作品曾在罗马万国博览会以及国内多种重要美术展览会中获奖。他的学生人才济济,如木岛樱谷和上田万秋。高剑父的弟弟高奇峰和高剑僧那些以“鹿”为题材的作品,即大多以樱谷同类题材作品为蓝本。《梅岭画谱》“花鸟部”第一辑初版于明治十九年,作者幸野梅岭(1844—1895),日本圆山、四条派著名画家,是日本第一所公立绘画学校“京都府画学校”的倡建者。他的学生很多,著名者如菊池芳文、竹内栖凤、都路华香、谷口香峤、上村松园等等,都是当年京都画坛出类拔萃的人物,高氏兄弟深受梅岭一系的画风影响,此不赘。
〔7〕参阅万青力《关于笔墨等于零的论争——致刘骁纯博士的一封信》,《画家与画史》,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第89—91页。
〔8〕林风眠在欧洲的经历,是这方面一个最著名的例子。参阅林风眠《我的兴趣》(《东方杂志》第3卷第1号,1936年)、《回忆与怀念》(《新民晚报》1963年6月27日)。
〔9〕“高剑父在中印联合美术展览会上的演讲辞”,《广州市政日报》,1931年6月27日。
〔10〕我们不应该忽略,像黄宾虹这样著名的“传统派”画家,在20世纪初叶“欧云墨雨,西化东渐”之际,也居然认为西方写实绘画与“北宗诸画,尤相印合”,希望借助摄影术达到“远法古人、近师造物”的功效。(参阅黄宾虹《真相画报叙》,《真相画报》第二期,1912年,上海)注意摄影术在中西绘画领域引起的不同反应及其后果,显然有助于加深我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
〔11〕贡布里希《阿佩莱斯的遗产》,范景中编选《艺术与人文科学——贡布里希文选》,浙江摄影出版社1989年版,第204页。




